8月23日,中國廣東核電集團(下稱“中廣核”)下屬的大亞灣、臺山、陽江、紅沿河、寧德、防城港6個核電站,同時舉辦核電站公眾開放日,共有700多人進入核電站內探訪。
7月,國務院公布《“十二五”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》,提出“到2015年,掌握先進核電技術,提高成套裝備制造能力,實現核電發展自主化;核電運行裝機達到4000萬千瓦”。
與沿用數年的《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(2005-2020年)》相比,4000萬千瓦核電的目標從2020年提前到了2015年。
不過,對中國而言,核燃料的保障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絲毫緩解。有學者預計,2020年中國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.36萬噸,2010-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.07萬噸。但國內開采成本低于130美元/千克的鈾礦儲量,目前僅為17.14萬噸,這意味著國內大部分的鈾礦需求將依賴進口。
“貧鈾”的中國
鈾礦儲量17.14萬噸。這一數據來源于經合組織核能機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在2010年7月正式發布的2009年版鈾紅皮書《2009鈾:資源、產量和需求》。事實上,中國此前沒有任何機構正式公布過相關數據。
“紅皮書的準確性是得到大家公認的,但由于鈾礦的勘查需要很長的時間,所以最新發現的一些大礦,并不會那么快就能準確掌握儲量數字,因此紅皮書的數據,肯定是比實際儲量要少。”中國核工業地質局科技處處長簡曉飛如此解釋。
多年以來,中國一直被定位為貧鈾國。2009年版的鈾紅皮書數據還顯示,澳大利亞、加拿大、哈薩克斯坦三國共占有全球52%的可開采鈾礦資源,而中國僅占有其中的3%,排在第十位。
顯然,與廣大的地域面積相比,3%的儲量并不相稱。“儲量數據一直在變化,幾年前很多人都接受的數據是,中國僅有7萬噸左右的鈾礦儲量。”簡曉飛說,“但現在這一數據擴大了一倍不止,儲量突飛猛進的原因不是特大礦床的發現,而是技術的進步。”
簡曉飛介紹,開采費用低于130美元/千克是國際上沿用多年的標準,高于這一成本的鈾礦并非無法開采,只是因為開采難度較高,缺乏商業價值,因而暫不作統計。
“隨著中國在鈾礦開采技術的提高,很多鈾礦的開采成本就會降低到130美元以下,也有了開采的價值,所以也被列入了統計。”簡曉飛說,“比如現在逐漸被采用的地浸采礦技術,使鈾礦的邊界品位由0.03%降到0.01%,原來選擇放棄的礦化圍巖,變成了可以利用的礦石,我們的鈾資源量自然就擴大了很多。”
盡管如此,中國的天然鈾生產幾年來鮮有增長。2004年,中國生產天然鈾當量為750噸,直到2010年才增加到產量827噸,產能為1350噸,但當年的鈾礦需求就達到了2875噸,缺口在2000噸以上。
鈾礦需求缺口巨大
中國現有鈾礦的情況并不理想,在全國200余座鈾礦中,大部分為中小型礦床,而全球已知的、儲量規模在500噸以上的582個礦床中我國僅占10余個,并且礦石品位以中低品位居多。目前,僅有江西撫州、新疆伊寧兩地的鈾礦能達到300噸的產能。
今年6月,中核集團地礦事業部總工程師張金帶在一個論壇上曾測算,按照我國2020年投運7000萬千瓦、在建3000萬千瓦的規模測算,2020年當年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.36萬噸,2010-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.07萬噸。如果按天然鈾產品提前3年供貨考慮,2020年當年需要提供天然鈾1.67萬噸,2010-2020年累計需要提供天然鈾12.65萬噸。
張金帶一直主張,中國的鈾礦資源足夠支撐未來的核電發展,全國潛在鈾礦總量應在170萬噸以上,但他也不得不承認,中期內中國對鈾礦的需求缺口巨大。
一般情況下,地質勘探從普查到詳查再到正式提交儲量,需10年左右時間,而此后的礦山建設還需要4年左右時間。
“即使在幾年之內國內鈾礦勘查有新的重大發現,也難以在2020年前大規模供應市場,而2016-2018年期間鈾礦累計需求量就將超過我國現有資源量,面對急劇攀升的需求,鈾礦供應嚴重短缺很快就會出現,并且鈾礦對外依存度將迅速上升,導致我國能源供需格局的重大變化。”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博士閆強分析道。
閆強認為,參股或者購入鈾礦出口國的鈾礦山是無法避免的選擇,但這將面臨不少競爭者,而同樣是貧鈾國并且渴望大規模發展核電的印度則將會是主要對手。
“鈾礦價格上漲肯定是不可避免的,但適度的價格上漲也有好處,鈾礦價格多年來一直低迷,也導致很多鈾礦企業動力不足,從世界范圍來看,鈾礦供需也有很大缺口。”閆強說。
2010年,全球鈾礦產量5.3萬噸,僅能滿足總需求的78%左右,剩下的只能通過庫存以及俄羅斯濃縮鈾稀釋產品來解決,未來必須尋找新的天然鈾來源。
鈾礦勘探仍有空白
最近幾年,鄂爾多斯盆地成為了國內礦業的焦點。在這一地區,發現了國內目前最大的鈾礦床,儲量可達數萬噸。
資料顯示,目前伊犁盆地南緣、吐哈盆地西南緣、鄂爾多斯盆地東北部、二連盆地中東部都已經建立了萬噸至數萬噸級鈾資源勘查基地。這些大礦都位于北方。
正是基于這些新的發現,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陳炳德不久前表示,我國鈾資源可能達百萬噸級,但勘查工作相對滯后,“潛在總量較大,前景廣闊,勘查程度較低,探明有限”。
對此張金帶并不回避,他曾表示,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,鈾礦地勘進入了長達15年的歷史低谷,直到“十一五”期間才得以恢復。在2001年前,地質找礦經費一度不到6000萬元,不到最高年份的1/15。
15年的低谷使得多年來鮮有大型新礦發現,現有的鈾礦產地大部分仍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發現。至今仍有360萬平方公里土地屬于鈾礦地勘的空白地區。
一位不愿具名的中核集團專家告訴時代周報,國家當年在發展核電問題上遲遲不下決心,建成大亞灣、秦山兩座電站后多年沒有決定下一步計劃,使得鈾礦的勘探隨之也放慢了下來。
“就地質條件來說,中國有著豐富的地質環境,尋找鈾礦應該是很優越的,我們臨近的蒙古、哈薩克斯坦跟中國的邊境地區都發現大量的鈾礦礦床,國內的新疆、內蒙古兩地與之相近的地質環境也很多,將來肯定會有更大的發現。”上述專家說。
公開數據顯示,中國在2009年用于鈾勘查的費用是4017萬美元,而哈薩克斯坦則為1.3億美元,中國僅為哈薩克斯坦的1/3。
林賀(化名)是包頭一家地質隊的隊員,他向時代周報介紹,1999年地質隊屬地化之后,目前中核集團旗下僅有三個地質大隊,而中廣核則主要從國外買礦,并不在國內找礦。
“地方的地質隊當然也能找鈾礦,但是肯定會優先找當地所需要的資源,鈾礦對地方來說價值遠沒有煤礦大。中核的地質隊就沒有這樣的束縛,并且屬地化之后,很多原來不能去探的地方現在都能去了,所以這十年才會有新的發現。”林賀說。
由于儲量稀少,鈾礦的品位不高,因此鈾礦往往有大量的伴生礦,而這些伴生礦往往威脅到鈾礦的開采。
鄂爾多斯盆地的特大型鈾礦床在發現后,便讓許多核電人士感到焦急,原因是這個鈾礦與煤礦伴生,如果不盡快探明并開礦,煤礦礦權的擁有者并不會等候。
“由于煤炭資源開發規模大,建設速度快,這不僅將對鈾礦資源造成很大破壞,也會造成放射性環境污染。”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提案中,中核集團821廠長宋學斌提出,要對鄂爾多斯盆地的鈾礦進行“搶救”。
因為鈾礦位于煤礦的上方,為了保護鈾礦開發,中核集團在三年前與兩家大型煤企簽訂開采互不影響協議,在20年(局部地區為10年)內開采完鈾礦,但由于種種原因,目前尚處于詳查階段,離探明儲量開礦仍需數年時間。
“在鄂爾多斯這種地方,到處都是煤,如果不盡快動工,很快就會隨著煤礦開采被破壞掉。”林賀說,“等地方提供水電需要很長時間,搬運機器也要不少時間,所以這幾年下去鉆井勘探都叫“會戰”了,真正能用的時間很少。”
按照目前的架構,鄂爾多斯的地質隊在完成鈾礦的勘查之后,需要將鈾礦轉交中核集團的鈾礦企業,而勘查的經費則全靠國家投入。
“中核集團是轉企了,我們很快也會完成轉企,但轉企以后怎么運作,實在不知道,既然是企業,那么找礦肯定要有收入,但我們實際上又得靠撥款。如果完全是自負盈虧,這活肯定沒人肯干,投入大量成本之后卻找不到礦,這風險誰來承擔?只能是靠國家了。”林賀說。
快堆商業化路途漫長
在《“十二五”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》中,第三代核電技術(AP100)被列為未來首要發展的對象,同時,作為國家863計劃重大項目,第四代核電技術快中子堆(下稱“快堆”)也被列入了示范工程計劃。
僅僅在一年前,中國的快堆實驗項目才并網發電,中國成為第五個掌握快堆技術的國家,而在全球范圍內,目前也只有法國的快堆實現商業運營。
作為第四代核能系統的發展方向,快堆技術的推廣將消除缺乏核燃料的擔憂。此外,快堆技術可將核燃料的利用率用原來的3%提高到50%-60%,大大減少鈾礦的需求量,緊缺問題有望解決。
國際原子能機構曾估計,第四代核電技術推廣之后,核燃料將由原來的鈾235改為蘊藏量更為豐富的鈾238,并且原來使用后的乏燃料(又稱輻照核燃料)也能取出繼續發電,因此地球上儲藏的鈾資源可供使用1000年,而乏燃料儲存所帶來的環保問題也能相應解決。
目前,中國僅有13個在運核電機組,產生的乏燃料有限,基本上存于核電站之內。在美國尤卡山地質處置場現存5萬噸乏燃料。乏燃料在數十萬年后才能降到天然鈾的毒性以下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曾表示,快堆要想商業化,必須具備經濟性和技術上成熟,目前快堆技術在國際上還處于試驗階段,預期2025年-2035年才能進入商用階段。
在快堆商業化之前,即20年之內,尋找鈾礦仍是發展核電所帶來最大的難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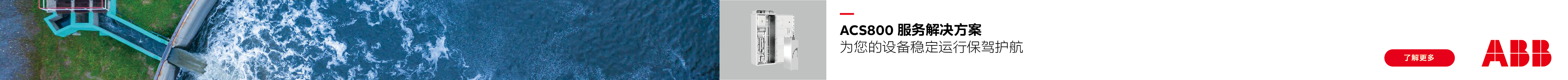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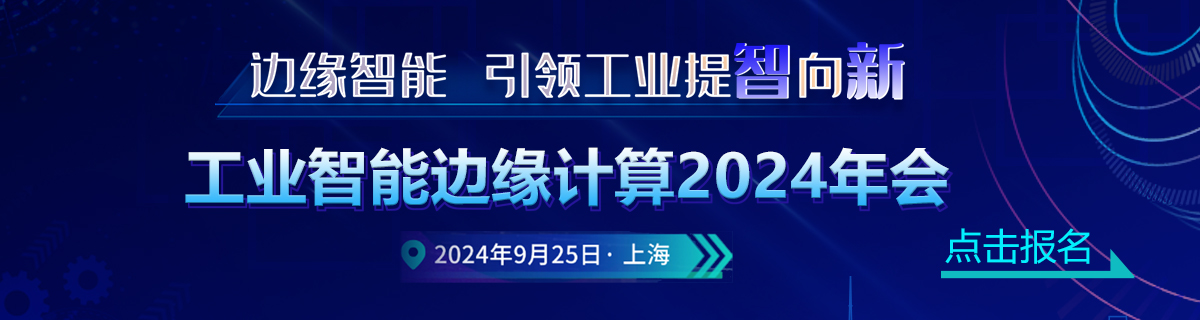


 資訊頻道
資訊頻道